话说童年最初的梦想
回忆童年时顺带想起的一件事,值得作一个补记。这件事不算是印象深刻的“场景”,因为我现在对此事的回忆其实已是间接的了,是因为这件事后来多次被我记起和说起,所以我确信此事不假。 话说从小学到高三,若要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的回答大概都会是:“科学家”。具体而言,小学和初中主要受奥数影响,偏向于数学家;后来看了诸多前沿物理学的科普书,就更倾向于物理学家。无论如何,直到我迫于无奈沦落进了哲学系,才开始认真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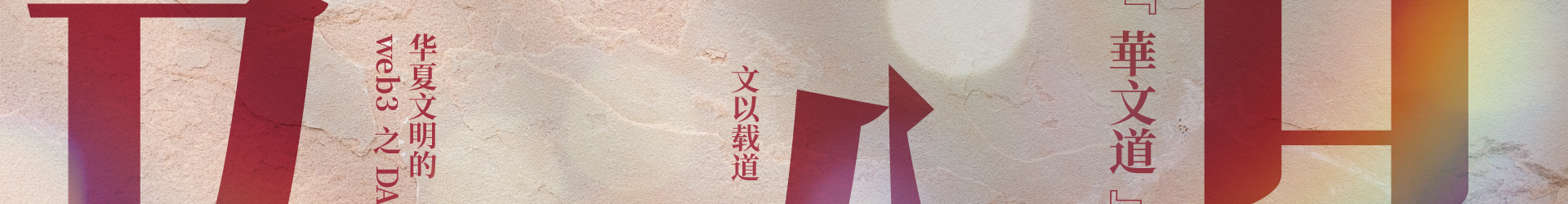
比较随意的学术写作,随想或杂文之类。
回忆童年时顺带想起的一件事,值得作一个补记。这件事不算是印象深刻的“场景”,因为我现在对此事的回忆其实已是间接的了,是因为这件事后来多次被我记起和说起,所以我确信此事不假。 话说从小学到高三,若要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的回答大概都会是:“科学家”。具体而言,小学和初中主要受奥数影响,偏向于数学家;后来看了诸多前沿物理学的科普书,就更倾向于物理学家。无论如何,直到我迫于无奈沦落进了哲学系,才开始认真考 …
回顾我的成长历程,可以勾勒出一条“明线”,大致包括珠算、奥数、薛定谔的猫、哲学大统一、生态哲学、康德等等这样一条线索。其中每一个事件都标志着某些明显的转折或发展。但也许更重要的事件并不是这些影响显明的,而是那些当时虽然看不出多大的影响,但这些事件仿佛刻印在心中,至今持续不断地对我产生着某些隐秘的影响的感受性的经历。格致中学天文台的星空体验当然是一例,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例“神启”式的重要体验,也就是说 …
之前提到我感觉被“命运”善意地捉弄之类,在以前的文章中或许也用过类似的修辞,嗯,这与我说“康德的阴魂在背后戳我”之类的话类似,只是用一种比喻性的修辞来表达一种“感觉”,并不代表我信奉“命运”,当然也不代表我不信命运,对于不明不白的概念,对它作一个是/否的判断总是没啥意思的。 首先我愿意声明的是,对于超验的神灵世界,我大概算是不可知论者。我既不会肯定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也不会断然否认它们。当我在谈 …
想到最新版的古派哲学之“旗号”。可以叫“关系主义”或“交流哲学”。 我早前偏爱“多元主义”、“视角主义”,而觉得“相对主义”过于极端或激烈。但现在突然想到,所谓“相对主义”(relativism)何不翻译成“关系主义”?这更符合“relate”的原意,也能够表达一种更对我胃口的思路。 说起“相对主义”,有人就要吼:“哈?一切都是相对的?”但如果我说“一切都是有关系的”,感觉是否颇为不同?如果说“绝 …
我总说我的哲学“从古典出发”,具体来说,大致从康德及其附近出发。不过这只是一种外在的解释,至于这个“古典”究竟有什么内涵,我是有自己的理解的。 在我看来,所谓“古典哲学”代表一种风格和态度,这种风格或态度由一整个时代所标志。粗略来说,西方哲学史划分为四个时代吧:古代(古希腊)、中古(中世纪)、古典时期、现代。——当然我这个“古典”是classical而不是ancient,“经典”义。更粗略的划分就 …
以下是我在“我不会在咖啡馆约会”后的评论中我被逼出来的一些说法,既然写出来了,就是白纸黑字,没办法了。鉴于这是一个不小的话题,因此专门开辟新文存档。 后来比我还邪恶的Chern同学说我这个是“女哲学家养成计划”,此题有趣,但太易引起误解。我的阴谋非常复杂,既不是要诱拐mm,也不是要培养女哲学家,更不是要找一个成为女哲学家的mm。但确实和各方面欲求都有联系,而最根本的宗旨始终是完善我自己的哲学。但说 …
这学期准备开啃康德的第三批判了,每次来咖啡馆时都把那块砖头带着,可惜至今还没有迎来开卷的冲动,所以……再说吧…… 无论如何,近些天康德的阴魂似乎总在我身边盘旋,时不时地戳我一下,仿佛在埋怨我怎么把他给冷落了…… 大二时写“同一片星空”讨论康德的科学与宗教,标志着我真正被拐进哲学之门; 大三时写“消极的本体论”讨论康德的第一批判,标志着我确定把康德认作自己的“起点”。 大四毕业论文写“康德伦理学…… …
最近我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说哲学是一种吐嘈的活动,我将大胆地在我的哲学中启用这一“术语”,它确实非常传神。 常看日本动画的人不会不知道“吐嘈”一词,不过“外行”和新手恐怕就不明白究竟了,我大致解释一下。 目前网上流传的解释似乎都是把POPGO字幕组的一段话到处复制,真是太偷懒了,这个可以去查百度百科之类,我结合一些网上容易找到的资料用自己的话简单再说一遍: 吐嘈一词是中文动漫字幕组对日语“突っ込み” …
我们说哲学的核心是“问题”,哲学的使命是“发问”等等,但究竟哲学是一种怎样的发问活动?“今天晚饭吃什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哲学的事情,那么哲学的发问究竟是怎样的? 相关的话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是提到过的,本文也许没有太多新意,只是一个回顾或总结吧。 首先,人们经常谈论所谓的“问题意识”,这个词被用得很滥,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地方干脆把它等同于“问题”来使用,比如“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是……”意 …
我只是一个在嘈杂喧闹的市井街头用随手拾得的最粗鄙的道具向匆匆而过的路人们耍弄着最低俗的戏法只是希望忙碌的现代人偶尔驻足片刻的无人捧场的卖艺人。 ——古雴 他既不是目中无人,也不是目中有人,他只是努力追寻真正的智慧。一个真正的小丑和其他纸牌是大不相同的。 ——苏菲 所以,苏菲,你现在必须做个选择。你是个还没有被世界磨掉好奇心的孩子?还是一个永远不会如此的哲学家? ——《苏菲的世界》 前一篇“海贼船的 …
钮拉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大致是说科学就像是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如果它出了问题,人们也只能用现成的或可以在海中拾得的东西来修补,或许你可以说把船整个拆掉重装更好,但问题是现在在茫茫大海中这艘船就是我们的立足之地,只能边航行边修补。 这个比喻是不错的,然而那些科学哲学家们并没有充分注意到的是,科学并不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孤立的、自由漂泊的东西,它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其它进程总是密不可分的,也许不是将 …
天知道为什么在若干篇毫无头绪的论文的压迫中我还有心思写那么多随笔,但没办法,想泻时憋住是很难受的。写完这一篇,这一轮发泄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也就是说,从“从渔夫到海贼”一篇起至这一篇,可以说是一个系列,可以理解为起航前最后的抱怨。从此之后……呼~反正我不再在宫殿中坐等了。 这一篇起了个扎眼的标题,其实试图谈论的东西是相当重要和深刻的,更准确一点的题目也许是“哲学与艺术”。无论如何,我现在只是起个头, …